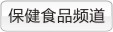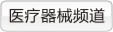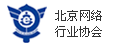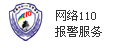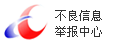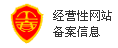中藥注射液: 不僅謀財,而且害命!
中藥注射液雖然不能算西藥,卻用西藥的給藥方式,且是其中危險性最大的一種。注射給藥方式會使有害成分直接進入人體甚至血液循環,往往導致過敏反應,嚴重時會危及生命。
一位朋友,孩子經常頭疼腦熱跑醫院。他最頭大的一刻,是醫生開出一列中成藥方子。他只能咬緊牙關,告訴醫生“我們不要中藥”。
這時候,醫生往往拋來狐疑、蔑視甚至敵視的目光,審視良久,好像不敢相信,一個病人,居然敢于質疑救死扶傷的醫生的決定。朋友有時不免氣短服輸,但一出醫院的門,馬上把這些藥扔進垃圾桶。如果是中藥注射液,比如喜炎平、熱毒寧之類,拋棄速度還要再翻一番。
有類似經驗的朋友,還很多。
1
這些朋友若知道下面這條新聞,面對醫生的審視,或許底氣會足一點。
 ▲饒毅
▲饒毅前不久,北京大學講席教授、中樞神經科學領域專家饒毅,在一個活動發言中指斥:“現在有一批中藥廠要大量向全國推銷中藥,甚至在全中國每年有幾千億的銷售是中醫注射劑,這是徹頭徹尾的偽科學。不是為了我們中國人民的福祉,是為了謀財害命。”
上述立場,對篤信中醫藥的朋友,或又構成冒犯,而旁觀多年“中醫藥值不值得信”的爭論,我已經很確信,這是短時間內撕不完的官司。所以本文收縮陣線,主要談一談,對“謀財害命”這么嚴重的指控,中(醫)藥注射液服不服?
為什么是中藥注射液?因為嚴格來說,中藥注射液本來就不能算“中藥”。
沒錯,國家藥品生產批準文號明確規定了中藥注射液為“中成藥”。然而,照此規定,使用該類藥品時必須按照中醫理論辯證論治運用,可是在臨床上,中藥注射液幾乎都是以現代醫學模式運用的,運用者包括大量不具中醫理論基礎的醫生。
 ▲棒棒醫生“炮轟”中藥注射劑
▲棒棒醫生“炮轟”中藥注射劑網紅“棒棒醫生”舉過一個臨床常用的丹參注射液的例子。“丹參苦,微寒,屬心、肝經。”那么,哪位護士能把針頭插進“手少陰心經”而不是靜脈嗎?有效成分在人體內產生醫療效用的流程,難道不是通過循環系統行進到靶點,而非經絡么?與“四性五味、升降浮沉”有半毛錢關系嗎?一大類藥品,無論從制作方法、運用方式到給藥途徑,都不是中醫的,能算真正意義的“中成藥”嗎?
可是,中藥注射劑算“西藥”嗎?似乎也不能。
盡管在《中藥藥劑學》中,中藥注射劑的定義是“以中醫藥理論為指導,采用現代科學技術和方法,從中藥或復方中藥中提取有效物質制成的注射劑”,但是,它確實不能算是西藥。
有些與中醫相關的藥品,比如青蒿素,從用藥理論到制作手段,都是現代工藝,是化學藥,是“中國人發明的西藥”。
但中藥注射劑又不同。
中藥注射劑的基本機理,是提取中藥有效成分,但對大部分中藥注射劑來說,“有效成分”其實沒那么清楚——有效成分本身就是“非中醫概念”,所以很多中藥注射液,基本是一鍋燴地“提取”。
用個不完全準確的比喻,一鍋雞湯,澄清干制,成為一包粉末狀物“雞精”,就有點像“中藥注射液”;而知道了雞湯的“有效成分”是谷氨酸鈉,人工制取或合成來調味,就有些像“西藥”。
實際上“中”“西”藥的說法本身就跑偏了。
包括中醫在內的各地傳統醫學,都經歷過類似的歷史階段,包括英法德等地的傳統醫學也是如此,只不過后來,有些傳統醫學成功地進行了現代化。用煎熬方法獲取有效物質,再通過不同給藥方式運用,這個思路也非常自然。
18世紀人們用金雞納樹樹皮對付瘧疾,與中醫的手法非常接近,不過沒有那些玄而又玄的理論。后來,當“西醫”用現代技術鎖定奎寧后,就不再把金雞納樹皮當成寶貝。反之,如果是在中國,按照中藥注射劑的機理,現在應用更多的可能就是“金雞納注射液”,甚至是“金雞納青蒿復方注射液”了。
2
問題在于,中藥注射液雖然不能算西藥,卻用西藥的給藥方式,且是其中危險性最大的一種。注射給藥方式會使有害成分直接進入人體甚至血液循環,往往導致過敏反應,嚴重時會危及生命。其生產與推廣的方式也都是“西藥化”的。
與此同時,中藥注射液雖然也不能算嚴格意義的中成藥,卻成功地以“中成藥”的身份,回避掉了對所有現代醫藥來說都至關重要的要求,包括準確闡述原理與療效,動物實驗、人體臨床實驗,相當于既獲得了“中藥現代化”的可信度,又無需面對嚴格的安全性與有效性驗證。
這種豁免權達到了什么程度?試舉幾例。
在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2006年印發的文件《關于印發中藥、天然藥物處方藥說明書格式內容書寫要求及撰寫指導原則的通知》中,關于不良反應,是這樣規定的:“應當實事求是地詳細列出該藥品不良反應……尚不清楚有無不良反應的,可在該項下以‘尚不明確’來表述。”
關于臨床試驗:“2006年7月1日之后批準注冊的中藥、天然藥物,如申請藥品注冊時,經國家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準進行過臨床試驗的,應描述該藥品臨床試驗的概況……未按規定進行過臨床試驗的,可不列此項。”其余藥理毒理、藥代動力學等項,均有類似“可不列此項”的表述。
而在另一份文件中,更明文規定,有些“古代經典名方”中藥,可以僅僅通過“非臨床安全性”研究,就直接申報生產(但很周到地補充道:適用范圍不包括危重癥,不涉及孕婦、嬰幼兒等特殊用藥人群)。
 ▲中藥注射劑的危害不容小覷
▲中藥注射劑的危害不容小覷這種網開一面造成的后果,可以說觸目驚心。
2015年,全國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網絡共收到中藥注射劑報告12.7萬例次,其中嚴重報告9798例次(7.7%)。2015年中藥不良反應/ 事件報告中,注射劑占比例為51.3%。
報告數量排名前五名的藥品分別是:清開靈注射劑、參麥注射劑、血塞通注射劑、雙黃連注射劑、舒血寧注射劑。
2014年,全國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網絡共收到中藥注射劑報告(也是)12.7萬例次,其中嚴重報告占6.7%。報告數量排名前十名的藥品分別是:清開靈注射劑、參麥注射劑、雙黃連注射劑、血塞通注射劑、舒血寧注射劑、血栓通注射劑、丹參注射劑、香丹注射劑、生脈注射劑、痰熱清注射劑。
更早,2010年國家藥監局的不良藥物反應報告中,中成藥的不良反應排名前20名,其中中藥注射劑就占了17個。前三位分別是雙黃連注射劑、清開靈注射劑、參麥注射劑。嚴重藥品不良反應/事件報告中,中成藥排名前20位的品種均為中藥注射劑。
2011年度藥品不良反應報告顯示,中藥注射劑依然是中藥制劑的主要風險。不良反應/事件報告數量排名前3名的藥品分別是清開靈注射劑、雙黃連注射劑和參麥注射劑。
從2006年魚腥草等7種中藥注射劑發生嚴重不良事件,國家食品藥品監管部門暫停相關注射液的銷售使用,其后每年都有中藥注射液造成的嚴重不良反應事件。
而據《中國藥典》編委會執行委員周超凡說:“中藥注射劑的藥物不良反應遠遠不止這么多。報道出來的僅僅是冰山一角。很多縣級醫院、鄉衛生院發生的不良反應都不了了之。”
 ▲食藥總局公布的藥品不良反應排行榜
▲食藥總局公布的藥品不良反應排行榜可以看到,最遲從2010年起,中藥注射液就牢牢占據了藥物不良反應排行榜的前列。換句話說,中藥注射液毫無爭議地提升了藥品不良反應發生率,增加了患者的風險。
同時,排行榜前列變化不大——這么多年里,監管部門如果不能說無所作為,至少其所為沒有使狀況發生明顯改觀。
對中藥注射液的辯護意見主要在兩點:一是生產工藝“歷史性必然”的落后,以后會好的;二是,難道西藥就沒有不良反應么?
中藥注射液最需要控制的,是滅菌和不溶性微粒。不過,高溫殺菌可能會造成熱敏性有效成分破壞、水中不穩定和不溶性微粒析出,而由于大部分中藥注射液成分必然非常復雜(與西藥相比),控制難度極大。
西藥當然也有不良反應。有些藥品或治療方式,比如化療,對人體的傷害甚至極大。但是,這些藥品或治療方式的危害,是經過驗證,被提示、有預期的,患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病情,自行評估風險/收益,甚至孤注一擲。
但中藥注射液由于缺少明確信息,患者既不能忽視它的風險,又不能清楚地判定風險。一個患者可以在知情的情況下,選擇付出巨大健康代價保住性命,卻也可能在不知情、無預判的情況下,因為頭疼腦熱,被打了一針中藥注射液過敏喪命。
哪個更讓人難以接受?
3
但我一向很“理解”食品藥品監管部門。它的監管能力,受到很多因素的掣肘。而對中藥注射液來說,情況尤為復雜。
中藥注射液大概是為數不多的能在“前后兩個三十年”甚至更久的歷史時期,都很吃香的事物。
1940年前后,八路軍一二九師首創了“柴胡注射液”。1965年6月26日起,為響應“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”的號召,全國大搞中草藥群眾運動,至1980年代,出現了多達1400多種中藥注射劑。短時間內研制出這么多種新藥,在現代藥物史上絕無僅有。
其后,在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,中藥注射劑經歷了一個小低潮,甚至沒有進入1985年和1990年版的《中國藥典》。然而在1990年代之后,它不僅殺回主流,還大紅大紫。
 ▲號召“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”的海報
▲號召“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”的海報中國政府設立有國家中醫藥管理局。查一下中醫藥管理局相關領導最近幾年的發言,幾乎不涉中醫藥安全監督與質量管控,基本調子是“發展、壯大”。
2016年2月,國家衛生計生委、國家中醫藥管理局(后者是前者下屬單位)聯合下發了《關于加強中醫藥監督管理工作的意見》,在“創新監管方式”部分特別要求:“法律法規沒有規定的,一律不得擅自開展監督檢查。”
在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2008年發布的《關于印發中藥注冊管理補充規定的通知》中,第一條就是:為體現中醫藥特色,遵循中醫藥研究規律,繼承傳統,鼓勵創新,扶持促進中醫藥和民族醫藥事業發展,根據《藥品注冊管理辦法》,制定本補充規定。
你看,“特色”“傳統”“創新”“扶持”“民族”都有了,居然沒有看到“患者”“療效”與“安全”。
很多中藥注射劑的支持者,堅持“中”“西”對立的論述邏輯,甚至將對中醫的支持上升到國家民族、意識形態的高度,敝帚自珍尚且不足,恨不得立刻對西風東漸的“西醫體系”“亮劍”。
這甚至形成了一種新的“政治正確”。這種聲音,在最近的大風向里,不是音調降低而是拔高了。
 ▲縣域等級醫院銷售額份額TOP15產品中有6個是中藥注射液(來源:新康界公眾號)
▲縣域等級醫院銷售額份額TOP15產品中有6個是中藥注射液(來源:新康界公眾號)近幾年,“新醫改”后對縣域醫院的財政支持增強,縣域醫院強勢崛起。“新康界”數據平臺的統計顯示,在包括氯化鈉、葡萄糖在內的縣域等級醫院銷售額份額TOP15產品中,有6個是中藥注射液。可見縣域醫院對中藥注射液的偏愛。
原因不難理解,與縣鄉醫院對不良反應的報告數遠低于實際水平在同一個邏輯線上。大城市的高等級醫院,情況就好得多。
據統計,早在2013年,排名靠前的28個中藥注射劑總市場規模就達350億元。幾乎每年“兩會”,都會有代表、委員提出要扶持中醫藥發展的問題。他們的身份,多數是中醫院院長或藥企老總。
2016年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,全國政協委員、北京順天德中醫醫院院長王承德說到現在中藥制劑審批程序繁冗,“一個新制劑要進入臨床應用,必須小白鼠點頭才能通過,而中醫藥專家的話都不算數。” “凡是藥都有毒性,越是有毒的藥越是好藥。”他還認為,現在各種管理限制越來越多,使得三分之一的中醫毒性藥沒有了,“(一旦)發生了中藥中毒的事,公安法院來管,有你醫療主管部門什么事?”
在當今中國的現實語境,試圖通過公開討論獲得中醫藥發展的根本共識,仍然近乎奢望。但對中藥注射液這個具體產品而言,它遠高于其他藥品的不安全性,藥理的不牢靠,都顯而易見。
由于國家層面對中醫藥產業的支持,很多中藥注射液上了醫保藥品目錄(盡管這兩年頗有減少),這實際上意味著用國家權威為這些有足夠可替代性的藥品背書。在國民生命的價值標桿面前,繼續保持對中藥注射液的監管無力,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明智。
更現實點說,包括中藥注射劑在內的所有中、西藥品,總是要“謀財”的,“謀財”的前提,是藥品有療效。藥品有不同程度的“副作用”,即都有可能“害命”,因而需要嚴格的驗證、監管體系。
但在療效與安全性都不能確定保證的情況下,對一種藥品的最低要求,恐怕只能是“盡管謀財,請勿害命”,就算是真的安慰劑,也已經不算壞了。

1、本網部分資訊為網上搜集轉載,為網友學習交流之用,不做其它商業用途,且均盡最大努力標明作者和出處。對于本網刊載作品涉及版權等問題的,請作者第一時間與本網站聯系,聯系郵箱:tignet@vip.163.com 本網站核實確認后會盡快予以妥當處理。對于本網轉載作品,并不意味著認同該作品的觀點或真實性。如其他媒體、網站或個人轉載使用,請與著作權人聯系,并自負法律責任。
2、凡本網注明"來源:虎網"的所有作品,版權均屬虎網所有,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、鏈接、轉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;已經本網授權的,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,且必須注明"來源:虎網"。違反上述聲明者,本網將追究其法律責任。

工業和信息化部ICP備案/許可證號:京ICP備12012273號-4
藥品醫療器械網絡信息服務備案號:(京)網藥械信息備字(2024)第00532號
虎網醫藥招商網(www.www.goldure.com)版權所有,謹防假冒